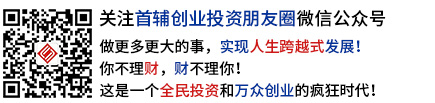仙居皤滩古镇的唐风宋韵

深秋的午后,阳光薄如蝉翼。在古镇皤滩的入口,我隐约看到了阳光中跳跃的斑点,它们迫不及待地,想为我讲述一个在历史的烟云中渐渐隐没的传说。宽阔的鹅卵石嵌图街面,我的脚印落在上面,尘土用微不可闻的声音歌唱,我一步步进入小镇丰繁复杂的内里。
如果你抬一抬眼,一定能看到公元998年的气象,这个繁华的年代,石子路上必然有无数商贾浪人摩肩接踵,像一幅巨大上演的宽屏幕,他们身穿古代的衣服,互相打着响亮的招呼。如果运气好,你还能看见和煦的春风吹着口哨,呼啸着涌进这个人流拥挤的小镇。花香飘漾,人们的脸上流露出盛世才有的明媚和光华。确实,彼时他们拥有足够骄傲的资本。因为从全国范围来讲,皤滩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商埠。
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皤滩乡,皤滩古镇距仙居县城西约25千米处。永安溪的河谷平原给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温润与饱满,又有万竹溪、朱姆溪、黄榆坑、九都港在此交汇,向下的水路直达椒江海口,向上的山道则通往浙西和赣南。自唐以来,皤滩古镇便是著名的盐商之埠。假设那是一个油菜花盛开的春日,浩浩荡荡的商船戴着满舱晒成的海盐逆流而上,直抵皤滩,然后改成身背肩扛,通过苍岭古道运往浙西以及内陆省份。
和镇上的老人闲聊,我听闻,皤滩最繁华时设有十多个地方专埠,如金华埠、永康埠、丽水埠、缙云埠、云和埠、龙泉埠等,食盐、布匹、陶瓷、药材、山货等物资均在皤滩埠头水陆中转。只消稍微想象一下,你就会被这份奢华大气、云蒸霞蔚所震撼:鹅卵石路上步履缭乱,尘土飞扬,人们带着数不清的货物和特产从全国各地奔赴至此,每当太阳升起,小镇上早已人声鼎沸,各种叫卖声、易货声不绝入耳。汇聚和流动产生文化的变迁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商贾和各方人士,在这里短暂地交汇,又从这里像撒网一样散向四面八方。古镇敞开博大的胸怀容纳了各方来宾。于是各种民俗风情孕育的多元文化,在皤滩古街上流动、沉淀。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我似乎闻到了咸湿的海水的味道。我手搭凉棚,眺望,水汽在眼前氤氲着蒸腾,场景轮换。
历史的风云荡涤了皤滩古镇的尘埃,也洗落了它曾经的韶华和风韵,似一位迟暮的美人,古镇不敌岁月的侵蚀,垂垂老去。如今走在街上,已经看不到当年鼎盛时期意气风发的风貌,举目望,皆是已然古旧的门庭,泛黄的门板斜斜地竖着,似乎一推就会向后倒去。路上静悄悄地,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,车子因为石子路面的颠簸惊起一阵阵“咯噔咯噔”的呼唤,像是划破记忆时空的一把利剑,把古镇从古代拉回现实。古镇静静地在这里,一寂百年,我猜它在等待,等待一个懂它的人,从这里路过,听它诉说满腔的衷肠。
继续迈着轻微的步子前行,我怕惊扰了古镇恬然的梦。出乎意料地,看似一截短街到了尽头,拐过直角又是一截短街,如此曲拐又曲拐,走过一街一重天,其感觉竟十分新奇有趣,颇有种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韵味。想必古街这样的拐曲造型并不是刻意为之,我用手抚过路旁灰旧的砖墙,耳边响起了刚听过的老人关于古镇街道造型的解释,街屋傍溪而建,屋后是船埠头,屋前便是临街的店铺,这样前店后埠的房屋建造格局,才形成了这样曲里拐弯的街形。皤滩“龙”形古街,东西长2公里,拐弯街道有9处为直角90度,街平均宽度3.5米,以鹅卵石镶嵌成各种图案。从街两旁的房屋建筑风格,以及多段街面石子拼嵌的图案看,九曲古街应该不是一气呵成的,而是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,在数个匠人的手下才形成了目前这样的九曲形状。
如果没有人文历史的积淀,皤滩古镇至多也只是个表面风光的美人,但正因有了深厚的人文底蕴,古镇从里到外透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温婉绵雅。
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陈氏祠堂,在暖阳下泛着微微的昏黄。我在靠近它之前,已听说了这个被古镇上的人传咏了近千年的故事。明亮的词像一只只张着翅膀漂亮的小鸟,从他们的嘴里争先恐后地跑出来。他们说,这是状元的府第。他们口中的状元,说的是一个叫陈正大的人。我可以想象金榜题名的那一天,那是宋嘉定十三年(公元一二二O年)的某一天,陈正大满面红光地跑回家,十年寒窗终于一朝鱼跃龙门,那是何等地激动与欢欣,那种令人痉挛的振奋,大概跟中举后的范进的心情差不多。当然,陈正大应该是比范进冷静得多,至少,他没有疯。在大殿高大的石柱上,刻着二十二副对联,其中一副对联这样写道:“家法守江州七百口,科名仰宋代第一人。”只可惜,史料上并没有记载陈正大是皤滩人,据说过去陈氏祠堂内的确挂有状元匾,不过现在此匾已不知去向。虽然不知这块匾遗落何处,但古镇人对于状元的推崇,是毫无疑问的。我看见,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,脸上闪现着骄傲的神采。
往前一点点,离陈氏祠堂不远,何氏里大学士府巍然而立。这座建于南宋,经明清不断修缮的院落,天井套天井,回廊接回廊,其秀丽典雅的建筑风格,如若还原当初姿态,一定不输苏州园林的纤巧。我眯起眼睛,翻开一些远去的典故,它们在何氏一族的生息过程中,代代相传。比如说,何氏族系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何焯。何焯生于皤滩,号荣仙,儒林称其义门先生,他是清代的著名学者,康熙钦赐翰林。何焯的书法在历史上颇有名气,与汪士宏(江苏苏州人,用笔挺劲)并称“汪何”,其《楷书桃花园诗轴》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。康熙五十四年(公元一七一五年),气宇轩昂的何焯率领大队人马来到皤滩,马蹄得得,爆竹喧鸣,“大学士”匾始挂于何氏里祖基厅堂,此后,何氏里被世人称为大学士府。何氏一族自宋朝以来,考中举人以上的就有十八人。在何氏大学士府里,就有一捷报厅,厅内四壁十数张捷报还依稀可辨。我想那时候皤滩的上空,一定是瑞气冲天或者祥云环绕。无数个阴雨或者天气晴好的日子里,时常会有衙门里“报房”的“报子”高举红榜,吆喝的声音绕过一条条长街,掠过斑驳的砖墙,比脚步更快地抵达何氏的某座台门大屋中。报,恭喜何大人高中……
从前听闻,在皤滩古街上走,一不小心便会踢翻唐宋石子,碰落明清匾额。古街上的匾额既是历史的象征,又是风云的见证。在九曲古街上周游了一圈之后,我的视线最终落到了其中闪着特别“光芒”的两块大匾,那便是“贻厚堂”匾与“洛社名高”匾。
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两块匾,它们的来头都不小。虽说“贻厚堂”的屋子不大,昔日的豪宅也落不下几分姿色,但它的主人则是清代著名文人陈瓒璜。送这块匾的人是谁呢?他就是匾上落款“桐城张若震”。即便文史知识有限,我也知道“桐城派”当年在清代掀起了一阵别树一帜的散文学风。由于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都是桐城人,后来人们就方便地把他们和追随他们的一群作家称为“桐城派”。桐城派主要宣扬和维护程朱理学为文学创作思想,张若震即是当时桐城派的一位有影响的散文家。那一年,陈瓒璜六十大寿,喜气洋洋的日子里,张若震带领一众家眷前来贺寿,仆人端上书有“贻厚堂”的牌匾,拙朴的名配上典雅的字,实乃令人赏心悦目之至。一时间,觥筹交错,主宾尽欢。
夕阳透过屋中间的缝隙漏下来,丝丝缕缕,像金线串起古屋的前世今生。在陈瓒璜古居中堂内,高挂的还有一块匾即“洛社名高”匾。要说送这块匾的人来头就更大了。这位大家名叫齐召南,号琼天,天台人,曾是乾隆太子宏瞻的老师,官至礼部侍郎。一生著作甚丰,其《水道提纲》被誉为河流巨著。那么“洛社名高”是什么意思呢?原来,这是颂赞陈瓒璜在洛社里的声望高远。所谓“洛社”,即研究“洛学”的一种组织。小时候的课本这样教导我们:北宋的程颢、程颐开宋代理学之先河,而南宋的朱熹继承和发展了“二程”的理学思想,于是后人习称这一学派为“程朱学派”。又因为“二程”是河南洛阳人,故又把之称为“洛学”。数十年前,两位英俊帅气的小伙一见如故,同拜恩师名下,共为学习研究“洛学”奉献青春,这是理想的呼唤,也是现实的感召。齐召南与陈瓒璜,同出师门的学友,情义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深长。也是在陈瓒璜六十大寿时,齐召南送了此匾贺寿,惺惺相惜两人多年的友谊。
天色渐晚,皤滩古街两旁的屋檐下挂起了形状各异的红灯笼,给古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暧昧。关于古镇的故事,还有很多,我走过一圈,大概只听闻了冰山一角。随意地一瞥,我就能看到皤滩老宅院的门口贴着许多用谐音象征不同意义的镇符,比如:蝙蝠,代表着开门纳福;鹿,象征着禄位高登;鱼,预示着吉庆有鱼,等等。而皤滩人灵巧的双手又为这些形象作了最生动的雕刻注释。俯仰间,那些古旧高立的围墙、迂回曲折的走廊、玲珑多姿的飞檐、黑色的瓦当、沧桑的木斗拱、精致的老雕刻……那一座座的古老宅院,在一年复一年的静默中书写着皤滩人居住的历史。
快要离开的时候,我在一个转身的时间里突然想到:与周庄、乌镇等相比,皤滩真是显得太低调了,低调得似乎你必须很用心,才能发现它曾经的辉煌。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件期盼之外的好事呢?毕竟它的存在,不是为了讨好谁谁谁;它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,值得一翻再翻。
当我行走在皤滩镇古建筑群的鹅卵石路上时,想象自己是在某页发黄的书本上爬行的蚂蚁,在砖与瓦的缝隙中倾听古镇隐秘的心跳声,那散落遍地的唐风宋韵,正迎面而来。
(编辑整理:仙居房产网)